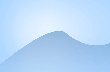范文澜论唐代文明互鉴1
1. 不怕事多,只怕多事。
2. 积金遗于子孙,子孙未必能守;积书于子孙,子孙未必能读。不如积阴德于冥冥之中,此乃万世传家之宝训也。
3. 能付出爱心就是福,能消除烦恼就是慧。
4. 身安不如心安,屋宽不如心宽。
5. 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
6. 恶是犁头,善是泥,善人常被恶人欺,铁打犁头年年坏,未见田中换烂泥。
7. 圣人求心,不求佛;愚人求佛不求心。
8. 人为善,福虽未至,祸已远离;人为恶,祸虽未至,福已远离。
9. 智者知幻即离,愚者以幻为真。
10. 诽谤别人,就象含血喷人,先污染了自己的嘴巴。
11. 恨别人,痛苦的却是自己。
12. 凡夫转境不转心。圣人转心不转境。
13. 知“因果”即知进退。知佛法,即得开心果。
14. 寒山问拾得:世人有人谤我、欺我、辱我、笑我、轻我、贱我,我当如何处之?拾得曰:只要忍他、避他、由他、耐他、不要理他,再过几年,你且看他。
15. 积德为产业,强胜于美宅良田。
16. 不妄求,则心安,不妄做,则身安。
17. 不自重者,取辱。不自长者,取祸。不自满者,受益。不自足者,博闻。
18. 征服世界,并不伟大,一个人能征服自己,才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
19. 把自己的欲望降到最低点,把自己的理性升华到最高点,就是圣人。
20. 嫉妒别人,仇视异己,就等于把生命交给别人。
21. 一个人如果不被恶习所染,幸福近矣。
22. 事不三思总有败,人能百忍自无忧。
23. 是非以不辩为解脱,烦恼以忍辱为智慧,办事以尽力为有功。
24. 万事得成于忍,与其能辩,不如能忍。
25. 伤人之语,如水覆地,难以挽回。
26. 欲知过去世,今生受者是。欲知来世果,今生做者是。
27. 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
28. 气是无明火,忍是敌灾星,但留方寸地,把于子孙耕。
29. 你能把“忍”功夫做到多大,你将来的事业就能成就多大。
30. 屈己者,能处众,好胜者,必遇敌。
31. 时时好心,就是时时好日。
32. 罗马人凯撒大帝,威震欧亚非三大陆,临终告诉侍者说:“请把我的双手放在棺材外面,让世人看看, 伟大如我凯撒者,死后也是两手空空。
33. 梦中冥冥有乐趣,觉后空空无大千。
34. 儿孙自有儿孙福,莫为儿孙做远忧。
35. 情生智隔。
36. 真正的布施,是把烦恼、忧虑、分别、执着、通通放下。
37. 一念放下,万般自在。
38. 学佛就是学做人。佛法,就是完成生命觉醒的方法,修行,就是修正自己的行为、思想、见解。
39. 话多不如话少,话少不如话好。
40. 得理要饶人,理直气要和。
范文澜论唐代文明互鉴2
《中国通史》是民国时期三大史学家张荫麟、蒋廷黻(fu)、吕思勉的汇编成果,本书以白话文的形式讲述了中国历代政治、宗教、社会文化、科学、思想等社会文明,重点描写了古代强大帝国兴衰历程以及百家争鸣的思想文化。古人云:读史可以让人明智,鉴以往可以知未来。或许那个狼烟四起、伴随着饥饿与寒冷的动荡年代已经不属于我们,但当我们向前看,回首历史,一种精神力量随之唤起:那就是以史为鉴,继往开来。
唐太宗李世民曾说过: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读《中国通史》,纵观上下五千年,每一个王朝都在“发展-繁荣-没落-灭亡”的轮回中被写进历史,从汉代的文景之治、唐代的开元盛世、明代的永宣盛世到清代的康乾盛世,均展现了古代人们开创美好生活的历程,然而,盛世过后,随之而来的就是国家的衰落与动荡,诸如:唐玄宗李隆基由于沉醉女色导致内乱爆发,万历皇帝朱翊钧30年不上朝使明帝国陷入危机,到了清代,清廷为换取一时苟安与列强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国人不应该也不可能忘记刻写在中国历史的镜头和片段,虽然斑斑点点但历历在目:从匈奴入侵到五胡乱华;从靖康之难到满清入关;从_战争到日本侵华战争;从“_”到“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正义与邪恶、文明与野蛮在这段历史中展现,时刻警示着我们每一位中华子女勿忘国耻、以史为鉴。
《中国通史》又以一段又一段的历史刻画出鲜明的历史人物,有孔孟的儒家之道,有杜甫的广厦万间,有_先生的天下为公,也有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豪情、冲冠一怒为红颜的无奈、秋风宝剑孤臣泪的悲痛。在此,给大家分享《中国通史》第六卷的一段历史体会,该卷讲述的是崇祯皇帝剿敌失败,李自成攻陷京师,吴三桂引清入关、清顺治帝入主中原等故事情节。每个主人公都有改变历史的契机:假如崇祯皇帝采纳左都御史李邦华南迁的建议,也许明王朝将在南方得以延续;假如李自成攻入北京后能够善待明朝遗老,吴三桂也许就不会复叛降清;假如吴三桂回京路上没有碰到自家家奴,也就不会有后来的山海关战役;假如多尔衮没有无意间的相遇,也就没有入主中原的时机。唯物史观告诉我们:对历史发展起决定作用的要素是社会生产力,但重要人物在关键时期做出的决定对历史的进程也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我们会深刻地铭记历史带给我们的教训。人言: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我们的人生就如同一部历史,在故事的一遍遍演绎中度过,当我们处在岔路口时该如何抉择呢?正如司马迁所说“迷往事,思来着”,历史将会给我们一个制高点,在成长的过程中给我们提供重要参考。
历史揭示了社会发展规律,为人类科学地认识过去与现在,为预见未来指明方向。如果不知道从哪里来,也必将在未来的发展中迷失方向,如果不知道封建王朝的腐朽没落,也不会去推翻封建制度,实现人民解放。在科学地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之后,才能科学的指导我们进行社会实践。因此,我们要要“以史为鉴、继往开来”。
范文澜论唐代文明互鉴3
中华文明之所以对外来文明与宗教表现出十分罕见的包容度,这与其世俗性的本质和文化自信密切相关。在汉代成为中华文明主脉的儒学是一套有关世俗社会伦理秩序的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接受这套文明规范的群体被视为“华夏”,尚未接受的群体被视为“蛮夷”,二者之间仅为“文明程度”的差异。
“中国的夷夏之辨……对外却有开放与封闭的两面,而且是以开放的一面为主流。夷夏之辨是以文野之分为基础的。……故夷夏也应该是可以互变的”。在与其他群体交流过程中,中华文明所持的是“有教无类”的立场,采用“教化”的方法来“化夷为夏”,而不是简单地排斥其他信仰与学说,因此中国人没有“异_”概念。在孔子的年代,中原地区居民的人种成分十分复杂,“所以,‘有教无类’主要不是指社会贫富等级差别,而是种族特征差别”,表示对不同祖先血缘及语言文化群体施以教化时应一视同仁。在对人类群体进行划分时,中华文明注重的是可涵盖“天下”所有人群、具有“普世性”的社会秩序与伦理规范,而不是其他文明所强调的体质、语言、宗教信仰差异等族群特征。在与异族交往中推行“教化”的方法是“施仁政”,“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主张以自身较高的文化修养和德行来对“蛮夷”进行感召,而不是使用武力手段强迫其他群体接受自己的文化。这种政策的前提是对中华文明的高度自信。“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孟子·公孙丑上》)。甚至连中国传统军事思想也强调“天子”的军队应为“仁义之师”,“不战而屈人之兵, 善之善者也”(《孙子》谋攻篇第三)。
因为不同文明之间可以相互学习与互鉴互融,所以中国传统思想认为“夷夏之辨”中的“化内”和“化外”可以相互转化。“‘天下’是绝对的,夷夏却是相对的,所需要辨认的,只是中原文明而已。血缘和种族是先天的、不可改变的,但文明却可以学习和模仿。因此,以华变夷,化狄为夏,不仅在中国历史中为常态,也是中华帝国文明扩张的使命所在。”“在古代观念上,四夷与诸夏实在有一个分别的标准,这个标准,不是‘血统’而是‘文化’。所谓‘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此即是以文化为华夷分别之明证,这里所谓文化,具体言之,则只是一种‘生活习惯与政治方式’。”夷夏之间存在的是一种动态与辩证的关系。“春秋之法,中国而用夷之道,即夷之,…… 以此见中国夷狄之判,圣人以其行,不限以地明矣。”因为中华传统的基本观念认为四周“蛮夷”与中原群体(“华夏”)同属一个“天下”且具有可被“教化”的前提,所以儒家提出“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的观念,明确淡化“天下”各群体之间在体质、族源、语言、宗教、习俗等文化领域差异的意义,强调不同人类群体在基本伦理和互动规则方面存在重要共性并完全能够做到“和而不同”与和睦共处。
儒学发源于中原地区并在后世以汉人为人口主体的中原皇朝占据主导地位,这一观点得到普遍接受。但是在中原地区与周边地区几千年持续的文化与政治互动中,儒学就完全没有吸收周边群体的文化元素而有所变化吗?孔子的思想本身就是在春秋时期“华夏”与“蛮夷”的文化与政治互动中产生的,这种文化互动自孔孟之后应当仍在延续,二程和朱熹的理学思想就明显受到外来佛教的影响。换言之,后世的儒学已不能被简单地视为“汉人之学”,而应当看作以中原地区文化传统为核心并吸收周边其他文化因素的“中华之学”。所以,如果把边疆_在“入主中原”后对儒学思想的吸收和尊崇(“儒家化”)等同于“汉化”,这样的观点就把中国历史上复杂的文化互动关系看得过于简单了。首先,我们不能把“儒学”简单地等同于“汉人文化”;其次,周边_(包括“入主中原”的异族_)吸收以儒学为主脉的中华文化传统的过程也包含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一个动态的吸收过程,周边_在不同时期对于中原文化有着不同的接纳态度和不同的吸收程度;另一方面周边_必然努力保持自身原有文化传统和群体认同意识。这是两种努力同时并行并相互影响的文化互动策略和文化交融模式。
范文澜论唐代文明互鉴4
1、一切皆为虚幻。
2、不可说。
3、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4、人生在世如身处荆棘之中,心不动,人不妄动,不动则不伤,如心动则人妄动,伤其身痛其骨,于是体会到世间诸般痛苦。
5、一花一世界,一佛一如来。
6、前生500次的回眸才换得今生的一次擦肩而过。
7、大悲无泪,大悟无言,大笑无声。
8、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9、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10、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11、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
12、苦海无涯,回头是岸。
13、前世五百年的回眸才换得今世的擦肩而过
14、为何不必?
15、一切皆为虚幻
16、不可说,不可说
17、菩提并无树,明镜亦无台,世本无一物,何处染尘埃!
18、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19、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20、一念愚即般若绝,一念智即般若生。
21、人生有八苦:生,老,病,死,爱别离,怨长久,求不得,放不下。
22、命由己造,相由心生,世间万物皆是化相,心不动,万物皆不动,心不变,万物皆不变。
23、笑着面对,不去埋怨。悠然,随心,随性,随缘。注定让一生改变的,只在百年后,那一朵花开的时间。
24、刹那便是永恒。
25、种如是因,收如是果,一切唯心造。
26、爱别离,怨憎会,撒手西归,全无是类。不过是满眼空花,一片虚幻。
27、由爱故生忧,由爱故生怖,若离于爱者,无忧亦无怖
28、以物物物,则物可物;以物物非物,则物非物。物不得名之功,名不得物之实,名物不实,是以物无物也。
29、人无善恶,善恶存乎尔心。
30、声在闻中,自有生灭。非为汝闻声生声灭,令汝闻性为有为无。
31、华严奥藏,法华秘髓,一切诸佛之心要,菩萨万行之指南,皆不出于此也。欲广叹述,穷劫莫尽,智者自当知之。
32、佛言:人系于妻子舍宅,甚于牢狱。牢狱有散释之期,妻子无远离之念。情爱于色,岂惮驱驰。虽有虎口之患,心存甘伏。投泥自溺,故曰凡夫。透得此门,出尘罗汉。
33、迦叶佛偈 一切众生性清净,从本无生无可灭。即此身心是幻生,幻化之中无罪福。
34、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35、心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
36、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若见世间过,即非真修者。
37、个个恋色贪财,尽是失人身之捷径;日日耽酒食肉,无非种地狱之深根。
38、真为生死,发菩提心。以深信愿,持佛名号。
39、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疑物,何处染尘埃。
40、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响。
41、缘起法身偈 诸法因缘生,我说是因缘。因缘尽故灭,我作如是说。
42、诸余罪中,杀业最重;诸功德中,放生第一
43、溪声便是广长舌,山色岂非清净身?
44、见色起淫心,报之在妻女。
45、报君今日是十六,念佛须当戒_。_断时生死断,便是如来亲眷属。
46、佛言:沙门行道,无如磨牛,身虽行道,心道不行。心道若行,何用行道。
47、拘那含牟尼佛偈 佛不见身知是佛,若实有知别无佛。智者能知罪性空,坦然不惧于生死。
48、毗婆尸佛偈 身从无相中受生,犹如幻出诸形像。幻人心识本来无,罪福皆空无所住。
49、七佛通诫偈 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
50、心如工画师,能画诸世间。五蕴悉从生,无法而不造。
51、罗衣偏罩脓血囊,锦被悉遮屎尿桶。
52、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
53、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54、若信愿坚固,临终一念十念,亦决得生。若无信愿,纵将名号持之风吹不入,雨打不湿,如铜墙铁壁相似,亦无得生之理。
范文澜论唐代文明互鉴5
试论唐代佛教寺院壁画的历史分期
一、初唐近百年的平缓发展期
从武德元年(618)到开元元年(713)的初唐近百年,是唐王朝政治、经济、文化稳定、巩固和拓展的时期,是步入盛唐人文发皇的准备阶段。“贞观之治”使李唐政治粗安,国力渐趋强大;安西、北庭二都护府远置于中亚地区,“胡越一家”四方辐凑使唐人的政治自负与文化视野大为扩展;经济上承杨隋余惠亦有长足之进步,以户计,则贞观初天下“不满三百万”〔1〕, 而中宗朝神龙元年已激增至“六百一十五万六千一百四十一户。”〔2〕
新王朝@①@①欲上的气象感染了这一代人的精神面貌。创作领域的士人们对梁陈以来“气骨都尽,刚健不闻”的艺术情趣大不以为然,“思革其敝,用光老业”〔3 〕以提倡一种使人奋发向上的刚健之美的文艺思想,在这一阶段已经肇兴。这对于初唐艺术的发展,以及在盛唐确立起一种恢弘博大,刚健有为的艺术风格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起点。然而,这种能得风气之先的敏感的思想,在初唐只能是一种预示。它还有待于历史的发展给其提供更为充分的.条件去展开。
唐初佛教,历太宗、高宗、武后朝,尤其是后者,终于取得了立足意识形态的地位。玄奘东归,义净藉东南海道返唐,唐代的译经之风再起。法相宗、律宗、净土宗、华严宗等佛教宗派在唐代社会各个阶层广泛传播,改变了初期“秃丁之诮,闾里甚传;胡鬼之谣,昌言酒席。”的局面,那种对佛教僧侣公开的贬贱和攻讦开始逐渐消失。士人学子,显宦贵胄游宿僧舍漫论三教已成为一种社会习尚。高宗上元元年诏曰:“公私斋会,及参集之处,道士、女冠在东;僧、尼在西,不须更为先后”。〔4〕武则天天授二年下制:“自今已后,释教宜在道法之上,缁服处黄冠之前。”〔5〕在不到20年的时间内, 佛教势力的迅速发展直接促动了这一阶段佛教寺院壁画的创作。
唐代佛教寺院壁画第一阶段是平缓发展期,它的第一个特征是对南北朝以来佛教寺院壁画的消化和吸收,并在这一基础上作出平缓的推进。
初唐画坛,阎氏兄弟颇负盛誉。李嗣真《后画品录》称:“博陵大安,难兄难弟。自江左顾、陆云亡,北朝子华长逝,象人之妙,号为中兴。”在二阎之中,阎立本的画艺又要高出一筹。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卷二《论名价品弟》中说:“必也手揣卷轴,口定贵贱……则董伯仁,展子虔、郑法士,杨子华、孙尚子、阎立本、吴道玄屏风一片,值金二万。”阎立本的艺术地位,与其善于多方面的吸收前人的经验是分不开的。史载“阎师张(僧繇),青出于蓝。”〔6 〕“阎立本至荆州,观张僧繇旧迹,曰:‘定虚得名耳。’明日又往,曰:‘犹近代佳手。’明日复往,曰:‘名下无虚士!’坐卧观之,留宿其下十余日,不能去。”〔7〕阎立本画艺的童蒙学习原本资于其父阎毗的北学传统,南北统一后,他对“南张”风格的学习显然存在一个疑而后学的过程。荆州“三观”,可以说是这一过程的一个缩影。
唐初画人对于南北朝以来中国绘画优秀遗产进行吸收消化乃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如当时活跃于佛教寺院壁画创作领域中的范长寿,其风格,其技巧史称其“博赡繁多”〔8〕; 靳智导“祖述(曹)仲达”但也能“改张琴瑟,变夷为夏。”〔9〕檀智敏师董伯仁界画, 表现建筑的阴阳向背能尽得物理,“屋木,楼台,出一代之制。”〔10〕继承
[1] [2] [3] [4]
范文澜论唐代文明互鉴6
试论唐代佛教寺院壁画的历史分期
一、初唐近百年的平缓发展期
从武德元年(618)到开元元年(713)的初唐近百年,是唐王朝政治、经济、文化稳定、巩固和拓展的时期,是步入盛唐人文发皇的准备阶段。“贞观之治”使李唐政治粗安,国力渐趋强大;安西、北庭二都护府远置于中亚地区,“胡越一家”四方辐凑使唐人的政治自负与文化视野大为扩展;经济上承杨隋余惠亦有长足之进步,以户计,则贞观初天下“不满三百万”〔1〕, 而中宗朝神龙元年已激增至“六百一十五万六千一百四十一户。”〔2〕
新王朝@①@①欲上的气象感染了这一代人的精神面貌。创作领域的士人们对梁陈以来“气骨都尽,刚健不闻”的艺术情趣大不以为然,“思革其敝,用光老业”〔3 〕以提倡一种使人奋发向上的刚健之美的文艺思想,在这一阶段已经肇兴。这对于初唐艺术的发展,以及在盛唐确立起一种恢弘博大,刚健有为的艺术风格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起点。然而,这种能得风气之先的敏感的思想,在初唐只能是一种预示。它还有待于历史的发展给其提供更为充分的条件去展开。
唐初佛教,历太宗、高宗、武后朝,尤其是后者,终于取得了立足意识形态的地位。玄奘东归,义净藉东南海道返唐,唐代的译经之风再起。法相宗、律宗、净土宗、华严宗等佛教宗派在唐代社会各个阶层广泛传播,改变了初期“秃丁之诮,闾里甚传;胡鬼之谣,昌言酒席。”的局面,那种对佛教僧侣公开的贬贱和攻讦开始逐渐消失。士人学子,显宦贵胄游宿僧舍漫论三教已成为一种社会习尚。高宗上元元年诏曰:“公私斋会,及参集之处,道士、女冠在东;僧、尼在西,不须更为先后”。〔4〕武则天天授二年下制:“自今已后,释教宜在道法之上,缁服处黄冠之前。”〔5〕在不到的时间内, 佛教势力的迅速发展直接促动了这一阶段佛教寺院壁画的创作。
唐代佛教寺院壁画第一阶段是平缓发展期,它的第一个特征是对南北朝以来佛教寺院壁画的消化和吸收,并在这一基础上作出平缓的推进。
初唐画坛,阎氏兄弟颇负盛誉。李嗣真《后画品录》称:“博陵大安,难兄难弟。自江左顾、陆云亡,北朝子华长逝,象人之妙,号为中兴。”在二阎之中,阎立本的画艺又要高出一筹。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卷二《论名价品弟》中说:“必也手揣卷轴,口定贵贱……则董伯仁,展子虔、郑法士,杨子华、孙尚子、阎立本、吴道玄屏风一片,值金二万。”阎立本的艺术地位,与其善于多方面的吸收前人的经验是分不开的。史载“阎师张(僧繇),青出于蓝。”〔6 〕“阎立本至荆州,观张僧繇旧迹,曰:‘定虚得名耳。’明日又往,曰:‘犹近代佳手。’明日复往,曰:‘名下无虚士!’坐卧观之,留宿其下十余日,不能去。”〔7〕阎立本画艺的童蒙学习原本资于其父阎毗的北学传统,南北统一后,他对“南张”风格的学习显然存在一个疑而后学的过程。荆州“三观”,可以说是这一过程的一个缩影。
唐初画人对于南北朝以来中国绘画优秀遗产进行吸收消化乃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如当时活跃于佛教寺院壁画创作领域中的范长寿,其风格,其技巧史称其“博赡繁多”〔8〕; 靳智导“祖述(曹)仲达”但也能“改张琴瑟,变夷为夏。”〔9〕檀智敏师董伯仁界画, 表现建筑的阴阳向背能尽得物理,“屋木,楼台,出一代之制。”〔10〕继承以为发展的创作实践首先在唐初画坛展开了。
唐初画家注重学习前人的文化精神,是一种合逻辑、合历史的群体行为,它在完成隋代画家所没有完成的熔冶南北朝以来艺术成果的历史课题。唐王朝的再次统一,以及政治的巩固和国势的强大使这批画家生发了极大的热情和自信心,去看待历史上各区域性的艺术成就,去考察、总结并加以融汇。唐代绘画及其寺院壁画对传统的继承,在唐初画家中得到了最为集中的反映。这种总结和综合给唐代绘画发展奠定了广泛的传统基础,宋人郭若虚指出在“六朝三大家”与盛唐吴道子之间的“二阎”,是中国人物画发展链带上重要的一环。
阎立本以及唐初一代画人在连接南北朝及隋佛教寺院壁画与盛唐佛教寺院壁画中,具有桥梁作用。但这种作用的只是一种平缓的推进作用而已。他们注重形似,“工于写真”〔11〕状物高于达意;“骨气不足,遒媚有余”〔12〕还未能脱尽魏晋六朝纤巧萎糜之风,其基本精神是平庸的。阎等人之所以未有被后世论者推为“画圣”,奉为“宗师”,“家样”,不是因为他们的技巧不高,(事实上阎等人的传真技巧是很高的,尤其是阎立本笔底物象能“万象不失”〔13〕)但他们的作品毕竟缺少一种精神。他们在师古、摹古的前代遗产综合过程中走了一条形似多于神似,状物高于达意的创作道路,在对对象世界的表现中处于相对被动的位置。因而,关系颠倒了,创作便无法从自身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无法进入尚意、创意的风格发展阶段。真正的“唐风”在这儿还没有建立起来,他们是一些批判和整理故旧的综合派人物。
在初唐画苑中还有着一种散发着异域馨香的创作样式,这就是尉迟乙僧的凹凸法。关于尉迟的寺院壁画,朱景玄记曰:“今慈恩寺塔前功德,又凹凸花面中间千手眼大悲,精妙之状,不可名焉。又光宅寺七宝台后面画《降魔像》,千状万怪,实奇踪也。”〔14〕段成式记其《降魔变》曰:“变形三魔女,身若出壁。”〔15〕尉迟乙僧“师於父”〔16〕家学出身,具有浓厚的西域地区风格。元人汤@②记其传世卷轴说:“用色沉著,堆起绢素,而不隐指。”〔17〕他是一位以色彩为主要造型手段的画家。但他入唐以后,处在汉文化高度发展的长安城中,因此技法也感染了不少中国传统技法。张彦远记其用线:“小则用笔紧劲,如屈铁盘丝,大则洒落有气概。”〔18〕张彦
尉迟乙僧是初唐佛教寺院壁画创作的一位重要的画家,其作品形象和造型手段的异域色彩吸引了当时人们的关注。尽管他的作品形象“非中华之威仪”〔19〕但时人仍以“胡越一家”的文化含纳精神,将其作品推于“神品”之位。他所代表的一派对于盛唐大家风格的形成以及造型手段的丰富,影响不小。盛唐画坛上的泰斗人物吴道子也多少吸收了他的凹凸晕染技法,史称吴道子设色“於焦墨痕中,略施微染,自然超出绢素。”〔20〕这种吴风中的技法当与尉迟乙僧的凹凸晕染法有一定联系。
然而,尉迟乙僧作为一位深染印度佛教艺术的于阗国人,在唐代,他只是以一个异域画人的区域性风格代表进入中国画坛的,终究无法代表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国绘画,也无法冲破这长期发展而形成的创作形式。他以“中华罕继”〔21〕的艺术特点给中国传统画苑吹入了一股新风,然而却又无法深入其核心。他是初唐画苑新风派的代表人物。
初唐异民族画家新风派人物,画格迥异于传统。他们的创作引起了中国画人的注意,其造型方法的某些特点也渗进了中国古代绘画的壁垒。但它终究无法替代传统精神所酿就的传统形式。寓含着大千世界的“线”的旨趣,在“墨趣”未曾大兴之前是独主中国画坛的坛主。它由点而线,由线而面,变化多端,极富造型能力。它正处在发展期,生命力是强大的。新风派人物对传统形式中的合理部分进行了尝试性接近,然而却无法造其堂室而徘徊于外在的模仿。尉迟乙僧是新风派的殿最人物,在以开放为特点的唐代社会中,他充分地表现了他的艺术。其所具有的风格情趣,给初唐佛教寺院壁画增添了吉光片羽。然而,这种创作只是东渐艺术的历史延续而已,它终究无法改变初唐佛教寺院壁画平缓发展的特点。
唐代佛教寺院壁画在走向盛大发展的黄金时期之前,初唐的创作为它做了两个准备:一是对中国古代绘画及其佛教寺院壁画作了广泛的综合、溶冶,将传统中优秀的内容作了严肃整理后的传移;二是继续保持了外来艺术的引进,保持了魏晋迄隋以来佛教寺院壁画创作上的“非锁国”的开放特点。这两点准备,尤其是第一点的完成给盛唐画人的创作奠定了丰厚的传统基础,使他们能藉此而跃入更高的高度。
二、盛、中唐百余年的鼎盛发展期
开元、天宝年间是盛唐的历史,唐代佛教寺院壁画也于此步入了它的鼎盛发展阶段。这一时期,大唐的政治趋于稳定;“风雨时若,人和岁稔。”〔22〕经济得以长足发展,“是时海内富实,斗米之价,钱十三;青、齐间,斗@③三钱。绢一匹,钱二百。道路列肆,具酒肉以待行人;店有驿驴,行千里不持尺兵。”〔23〕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内部政治的稳定,使得这一时期的统治君王及其所代表的整个阶级,产生了一种向外拓展以播扬国威的强烈欲望。天宝元年,唐置十节度、经略使,领兵四十九万,马八万〔24〕,天宝六载,唐将高仙芝远征小勃律,这是中原王朝前史所无的一次最远的西征,它到达了今天的大小帕米尔高原一带。边战跨出了防御性的长城,历史上因边境民族的入侵而奋起的防御性边战转化成了向外拓展的进攻性边战。“古人重守边,今人重高勋。……誓开玄冥北,持以奉吾君。”〔25〕一种“功成画麟阁”〔26〕外求功利的精神弥漫于大唐的社会。
“开元盛世”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所取得的成功,给它的文化发展带来了极大的推动和刺激。如果说唐初文化发展具有整理、综合南北朝以来文化的特点,那么,盛唐文化则已经站在这一起点上进入了突破既往文化的创造性发展阶段,并逐步形成了一种恢弘博大,“焕烂而求备”的文化特点。盛唐时代的文化人在国势昌大,国威远扬,政治经济发达到最高峰的环境中生活、涵养,洋溢着一种自信,焕发出一种精神,他们充满了“群才属休明”就当“乘运共跃鳞”事业情趣;他们以一种“扬马激颓波,开流荡无垠”〔27〕的豪情与气派,开启了一场辉映古今的文化创造运动。
盛唐时期的佛教,虽经玄宗开元初年的抑制而稍有停顿。但由于佛教在与李唐统治阶级的长期携手中,已经形成了较为凝固的“同盟”关系。因此,不久它便又在统治阶级的支持下发展了起来。开元二十四年,玄宗颁赐《御注金刚般若经》〔28〕开元“二十六年六月一日,敕每州各以廓下定形胜寺观,改以开元为额。”“天宝三载三月,两京及天下诸郡,于开元观、开元寺,以金铜铸元宗等身、天尊及佛各一躯。”〔29〕“三教并崇”依然是盛唐时期意识形态的基本格局。
在中唐六十余年的历史中,李唐王朝的政治、经济的发展远没有盛唐来的昌盛。其文化的发展,在总体上也丧失了盛唐时代那种恢弘博大、高扬揭举的气势。“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欲演欲烈。建中四年“四藩称帝”,唐王朝几乎面临着“自国门之外,皆方镇矣。”〔30〕的严峻形势。内政方面,“宦官攘政”、“朋党交争”南衙北司如水火难以相容。统治阶级内部长期的权力斗争内耗了这个庞大的王朝的能量,整个统治开始步入了由盛转衰的下坡路。横跨唐朝盛衰两段历史的杜甫极其深沉地吟道:“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31〕旧籍记载,肃宗乾元元年,唐全国户数骤减为“一百九十三万三千一百七十四户”〔32〕此后,虽经德宗两税改制,宪宗收平淮西等镇。然而,至文宗大和年间,唐全国户数方才有“四百三十五万七千五百五十七户”〔33〕不及天宝十三载所计户数一半。
中唐社会尽管政治、经济已出现衰退的趋势,但统治阶级对佛教的支持依然是有增无减。肃宗时_大师不空“官至乡监,出入禁闼,势移权贵。”〔34〕政治**、国门报警,使得统治阶级对佛教的利用更趋频繁也更显荒诞,“或夷狄入寇,必合众沙门诵《护国王经》为禳厌,幸其去则横加赐与,不知纪极。”〔35〕宗教迷信在这个虚弱的时代里,堂而皇之地扮演着“护国神”的角色。
唐代佛教寺院壁画第二阶段,是其鼎盛发展期。在创作上涌现了大批高造诣的壁画艺术家,体现了成熟的技巧,并形成了具有典型时代意义的风格样式,“唐风”式的作品开始形成;创作在整体上走向繁荣,作品的数量较之初唐有了很大的增长;这一阶段也是创作门类最为齐全
这一阶段的佛教寺院壁画已经脱离了南北朝及隋以来的影响,进入了风格突破的创造发展阶段。宋人邵博《闻见后录》曰:“观汉李翕、王稚子、高贯方墓碑,多刻山林人物,乃知顾恺之、陆探微、宗处士辈有此遗法。至吴道元,绝艺入神,然始用巧思而古意灭矣。”盛唐时代中国绘画的风格发生重大变化的事实,邵博在比较中直觉地捕捉到了。但他将其归结为个人的巧思,却反映了他对艺术发展的认识是存在局限的。唐代佛教寺院壁画第二阶段发展的历史,说明这种风格的发展乃是群体的而非个体的。在这个鼎盛发展期,个人风格与流派一时蔚起,如同一座岩峰并岭,高秀半天的群山,而其庞大的创作群则正象那自岭下而指向八方的巨大的山根,支持着峻秀的峰峰峦峦。盛唐吴道子个人的巧思是这盛大发展中的一个典型,而绝非是全体。
吴道子是一位多产而优秀的佛教寺院壁画艺术家。史称其:“凡画人物、佛像、神鬼、禽兽、山水、台殿、草木皆冠绝于世,国朝第一。”〔36〕佛像及诸经变画尤为其所擅长,所成佛画样式,世称“吴家样”。这种吴风样式,笔力遒劲而畅快,“画衣裳,磊落生动。”〔37〕其长安菩提寺佛像“天衣飞扬,满壁风动。”资圣寺人物“出奇变态千万端”使人“dǔ@④之忽忽毛骨寒”。〔38〕现传世的《释迦降生图卷》上,无论是腾挪欲跃的神兽,还是髭须怒张的神人,笔里形间都洋溢着一种雄健外拓的精神。元人汤@②说:“唐人名手至多,吴道子笔法超妙,为百代画圣!”〔39〕吴道子画风中纵横健拔、高扬揭举的气势,昭示着盛唐画风的开始。